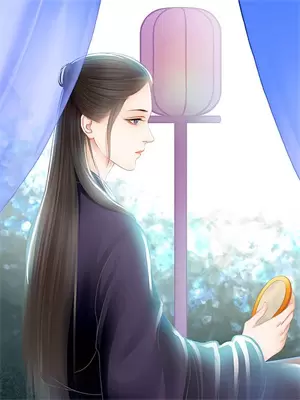1.死废物,开个车都不会,偏要逞能!我妈尖利的骂声穿透车窗,刺得我耳膜生疼。
我爸坐在副驾,脸色铁青,死死瞪着前方那支白幡飘飘的队伍。今天是我的婚礼,
婚车却在半路熄了火,不偏不倚,正对着一支送殡队伍的头车。黑色的棺材,巨大的遗像,
哀乐凄凄。一片慌乱中,没人记得用红布遮挡婚车头。这是大忌。开车的陈屿,
我的新婚丈夫,只是低着头,一遍遍地拧动钥匙。他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看起来比谁都紧张。
可我的心,却一点点沉了下去。陈屿是个赘婿。我家开了个小加工厂,前两年经营不善,
濒临破产,欠了一屁股债。是陈屿主动找上门,说他愿意入赘,不要一分彩礼,
只要我爸妈点头,他就能解决厂子的困境。他长相清俊,说话温吞,看着毫无攻击性,
却总给我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我爸妈走投无路,把他当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火速定下了婚事。此刻,我看着他那张写满无辜和慌张的脸,
一个荒谬的念头冒了出来。这场冲撞,真的是意外吗?送殡队伍缓缓走远,
车子也终于重新打着了火。婚礼在一片尴尬和晦气中继续。席间,我妈全程黑着脸,
指桑骂槐,说陈屿是个扫把星,给我家带来了霉运。陈屿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给我夹菜,
温顺得像一只没有爪牙的猫。可当晚,奇迹发生了。我爸接了个电话,
激动得差点把手机摔了。拿下了!城南那个大项目,指名要跟我们合作!
预付款明天就到账!那个项目,我们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摸到门槛,
如今却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砸了下来。我妈愣住了,随即狂喜,看陈屿的眼神都变了。
她拉着陈屿的手,第一次露出了笑脸:小屿啊,妈错怪你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星!
我看着这一幕,只觉得浑身发冷。福星陈屿带来的好运,远不止于此。第二天,
我路过彩票站,随手机选了一张,中了五百万头奖。我爸的厂子起死回生,订单接到手软,
短短一周,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还大赚了一笔。我家从破产边缘,
一跃成了邻里口中暴富的传奇。所有人都说我命好,旺夫。我妈更是把陈屿捧上了天,
豪车名表流水似的往他面前送,态度比对我这个亲生女儿还好。她私下里劝我:思思,
陈屿是你老公,你别老是板着个脸。你看他给我们家带来了多大的运气,你得对他好点。
我看着镜子里容光焕发的自己,心里却像是压着一块巨石。这一切,太顺了,顺得诡异。
我忘不了婚礼那天,陈屿在送殡队伍前,那双看似慌乱,实则平静无波的眼睛。
我也忘不了那场葬礼的主人公——本地商界赫赫有名的大佬,林宽。他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
新闻上说,死状惨烈。这天深夜,我被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惊醒。身边的陈屿不见了。
我披上衣服,悄悄走到院子里。月光下,陈屿蹲在角落,面前是一个火盆,里面正烧着黄纸。
他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他在念一个名字,一遍又一遍。
林宽……林宽……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他果然有问题。我冲了过去,一脚踢翻了火盆。
火星四溅,映出他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他抬起头看我,没有丝毫被撞破的惊慌,
眼神平静得可怕。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声音发抖。陈屿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他淡淡地说,我在借运。借运?
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跟一个死人借运?对。他承认得干脆利落,
婚礼是阴阳交汇的节点,红白喜事对冲,最容易打开气运的缺口。林宽是暴富横死的命格,
气运正盛,死后无人承接,白白散了可惜。他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
我用我们的婚事做饵,截了他的运,渡给你。思思,你不高兴吗?我看着他,
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不是窝囊废,他是个疯子。
一个用婚姻和人命做交易的疯子!你疯了!我尖叫起来,这是偷!是拿死人的东西!
那又如何?陈屿走近一步,轻轻抚上我的脸,指尖冰凉,厂子得救了,你也中奖了,
我们现在有钱了,这不就是你爸妈想要的吗?他的语气温柔,
可我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这是有代价的,对不对?我颤声问。陈屿的动作顿住了。
他深深地看着我,眼神复杂难辨。思思,别怕。他轻声说,一切有我。陈屿的话,
像是一剂毒药,暂时麻痹了我的神经。可恐惧的种子一旦种下,便会疯狂滋长。我开始失眠,
总觉得黑暗里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我的手腕上,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块小小的、硬币大小的青黑色印记,像是被人用力掐过,却怎么也揉不散。
我问陈屿,他只说是普通的淤青,过几天就好了。可那印记非但没有消退,
反而颜色越来越深,边缘也开始变得模糊,像是要融入我的皮肤里。我不敢告诉爸妈,
他们正沉浸在暴富的喜悦中,将陈屿奉若神明。我爸给陈屿在厂里安排了副总的职位,
实际上就是个闲差,每天喝喝茶看看报纸。我妈则张罗着给他买了一辆百万级别的豪车,
亲自把钥匙交到他手上,笑得满脸褶子。小屿啊,以后你就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思思要是敢欺负你,你跟妈说,妈给你做主!陈屿依旧是那副温顺谦和的样子,
对我爸妈言听计从,对我体贴入微。他越是这样,我心里的不安就越是浓重。一天,
我妈厂里的一个老员工,李婶,在操作机器时,不小心被卷进去了半只手掌。血肉模糊,
场面惨不忍睹。我爸妈赶到医院,赔了一大笔钱,才把事情压下去。晚上回家,
我妈心有余悸地抱怨:真是倒霉,厂里最近顺风顺水的,怎么偏偏出了这种事。
我坐在沙发上,手腕上的印记仿佛在灼烧。我猛地看向陈屿。他正低头削着苹果,闻言,
抬起头,对我露出了一个安抚的微笑。妈,别担心,意外而已。我已经找人看过,
厂里的风水没问题。他的话音刚落,我家的宠物猫团团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
发疯似的在客厅里乱窜,最后狠狠撞在墙上,抽搐两下,不动了。我妈吓得尖叫起来。
我冲过去抱起团团,它身体僵硬,已经没了呼吸。我抱着团团冰冷的尸体,
浑身发抖地看着陈屿。这也是意外吗?陈屿削苹果的手停住了,他没有看我,
只是盯着手里的水果刀,刀锋上反射着冰冷的光。思思,有得必有失。他轻声说,
我们得到的太多,总要还回去一点。还?用什么还?我的声音拔高,用一条命吗?
只是一只猫而已。他终于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你太紧张了。
我爸妈也被这诡异的气氛吓到了,我爸皱着眉呵斥我:苏思思!你怎么跟你老公说话的!
不就是死了一只猫吗?再买一只就是了!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无比陌生和寒冷。
他们被金钱蒙蔽了双眼,已经分不清是非对错。在这个家里,我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异类。
那晚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躲着陈屿。我搬到了客房去睡,他也没有反对,只是每天晚上,
都会在门口站很久。我不敢开灯,只能从门缝里,看着他被月光拉长的影子,
像一个沉默的鬼魂。家里的怪事越来越多。名贵的花瓶会自己从架子上掉下来摔碎,
新买的锦鲤会无缘无故地翻肚皮,就连我妈最爱的那只翡翠镯子,也莫名其妙地断成了两截。
每一次,陈屿都会用意外来解释。而我爸妈,在短暂的惊慌和心疼后,
很快就会被新的、更大的好运所安抚。厂里的利润翻着倍地涨,我爸甚至开始计划开分厂。
他们越来越依赖陈屿,越来越信服他的话。我手腕上的印记,已经扩散到了小臂,
颜色黑得像墨,皮肤下的血管都变成了青紫色,狰狞可怖。我开始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精神也日渐萎靡。我必须自救。我偷偷去了本市最有名的寺庙,求了一道平安符。
据说那里的主持德高望重,开过光的符咒最为灵验。我将符纸贴身藏好,
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可当我晚上回到家,推开卧室门时,
却闻到了一股檀香和纸灰混合的诡异味道。我的平安符,不知何时已经到了陈屿手上。
他坐在床边,指尖夹着那张已经烧成灰烬的符纸,轻轻一捻,黑色的灰末便簌簌落下。
思思,我说过,这些东西没用的。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你监视我?我只是担心你。他站起身,一步步向我走来,你最近状态很不好,
我不放心。他想来碰我,我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叫着后退。别碰我!
我的反应似乎刺痛了他,他脸上的平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
他眼底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绪,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为了我?
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为了我,就去偷死人的运气?为了我,
就看着家里的活物一个个死去?陈屿,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他低吼道,第一次在我面前失态,我想让你爸妈看得起我!我想让你不用再为钱发愁!
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像是在为我着想。可我看着他那双狂热的眼睛,只觉得毛骨悚然。
就在我们对峙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苏思思!你给我开门!
一个陌生的、充满戾气的男声响起。我和陈屿都是一愣。我爸妈闻声赶来,
隔着门问:你找谁?我们不认识你!我叫林泽。门外的男人冷笑一声,
我爸叫林宽。一个星期前,你们的婚车,撞上了我爸的葬礼。我说的对吗?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是林宽的儿子,他找上门来了。付费点门被我爸打开了。
林泽站在门口,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气质凌厉,
眼神像鹰一样锁定了客厅里的我和陈屿。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保镖,一看就来者不善。
林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爸陪着笑脸,想递上一根烟。林泽看都没看,
径直走了进来,目光在我手腕那片狰狞的青黑上停顿了一秒。我爸死后,
林家家运一落千丈,股票暴跌,项目被抢,连家里的风水鱼都死光了。他声音冰冷,
像是在陈述一件与他无关的事,我找人算了,说我爸的运,被人偷了。他顿了顿,
视线转向陈屿,嘴角勾起一抹嘲讽。偷运的人,就在那天冲撞葬礼的婚车上。
我爸妈的脸色瞬间变了。林先生,你别胡说八道!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些东西!
我妈尖声反驳,但明显底气不足。信不信不重要。林泽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重要的是,我查到,从那天起,
你们苏家的厂子就接到了我们林家谈了半年都没拿下的订单。苏小姐你,
还中了五百万的彩票。他每说一句,我爸妈的脸色就白一分。
我不管你们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林泽下了最后通牒,二十四小时之内,
把我林家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还回来。否则,我就让你们苏家,在榕城彻底消失。说完,
他不再多看我们一眼,转身带着人离开了。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