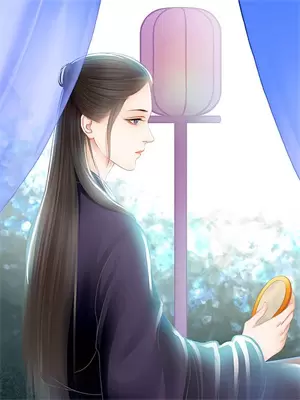邻居王建军每天凌晨两点准时剁肉馅,砰砰声回荡老楼。我忍了七天终于崩溃,
举着菜刀砸他家门。开门的是他六岁女儿,眼睛像蒙尘的玻璃珠。“爸爸在给我做小猪包子,
”她小声说,“可是我们家没有猪。”我瞥见案板上的肉馅泛着诡异的淡粉色,
飘来似曾相识的香气。01我叫林凡,在这栋破旧的老楼里已经住了三年。这楼有些年头了,
墙皮剥落得厉害,楼道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和各家各户油烟混杂的复杂气味。
住在这里的人,大多像我一样,是这座城市里不起眼的螺丝钉,
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有些喘不过气,蜷缩在这租金相对低廉的角落里,熬着一天又一天。
我的睡眠一直不算太好,有点声音就容易醒。所以,当隔壁新搬来的邻居王建军,
在第一个凌晨两点整,准时响起那“砰砰砰”的剁肉声时,
我几乎是瞬间就从浅眠中被拽了出来,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然后又猛地松开,
怦怦直跳。那声音太清晰了,仿佛就在我的枕边响起。厚重的实木砧板,沉甸甸的剁骨刀,
一下,又一下,富有节奏,力道均匀,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执着。声音在寂静的夜里,
在老楼空荡的楼道和房间之间碰撞、回荡,钻入耳朵,敲打在鼓膜上,震得人头皮发麻。
我捂住耳朵,用枕头盖住头,但那声音像是有了生命,无孔不入。它不仅仅是声音,
更像是一种实质的震动,通过床脚,通过墙壁,一丝不落地传递到我身上。
我能想象出那刀刃落在砧板上的情景,想象肉块在刀下被分解、碾碎,变成粘稠的肉糜。
第一晚,我忍着。初来乍到,也许人家有什么急事,或者就是生活习惯怪异了点。
邻里邻居的,不好第一天就撕破脸。第二晚,声音依旧准时在两点响起。我翻来覆去,
数羊数到几千只,那“砰砰”声依旧稳如磐石地穿透一切屏障。我坐起来,
在黑暗中瞪着那面传来声响的墙壁,胸口堵得发慌。第三晚,我试图用音乐对抗,戴上耳机,
把音量调到最大,但重金属的咆哮竟然也压不住那单调而执拗的剁肉声。
它仿佛自带一种穿透规则的属性,顽固地占据着我的听觉神经。第四晚,
我顶着两个浓重的黑眼圈,在白天敲响了王建军家的门。
开门的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有些瘦削,穿着朴素,甚至有点邋遢,
脸色是一种不太健康的苍白。他看人的眼神有些躲闪,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拘谨。
“那个……王先生是吧?”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和善,“我是隔壁的林凡。”“哦,
林先生,你好你好。”他搓着手,声音不高,带着点沙哑。“是这样,最近几天凌晨,
总听到有些……剁肉的声音?”我斟酌着用词,“声音有点大,我睡眠不太好,
所以……”他脸上露出一丝恍然,随即是歉意的笑,那笑容看起来有些疲惫,
甚至有点古怪的僵硬:“对不住,对不住啊林先生,我……我在一家包子铺帮工,白天忙,
只能晚上准备第二天的肉馅。真是对不住,影响你休息了。我尽量快点,尽量轻点。
”话说到这个份上,态度也算诚恳。一个为了生活熬夜干活的人,我还能多说什么?
难道还能逼着人家别干活了?我只能挤出一点理解的笑容:“哦,这样啊……理解,理解。
那……麻烦您尽量轻一点吧,谢谢了。”“哎,好,好,一定一定。”他连连点头,
关上了门。那天晚上,我怀着一点微弱的希望躺下。然而,凌晨两点,
那“砰砰”声依旧分秒不差地响起。力度,节奏,没有丝毫改变。我的希望破灭了,
心里涌起一股被愚弄的愤怒。但愤怒之后,是更深的无力和疲惫。第五晚,
第六晚……我感觉自己正在被这永无止境的噪音凌迟。白天工作昏昏沉沉,注意力无法集中,
对着电脑屏幕,眼前却总是晃动着想象中的剁刀和肉块。脾气变得暴躁易怒,
一点小事就能让我心头火起。我开始害怕夜晚的降临,
害怕那准时响起的、如同诅咒般的声音。到了第七天,我的精神已经绷紧到了极限。
太阳穴突突地跳着,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当窗外的夜色再次浓郁得化不开,
当时针一点点挪向那个恐怖的两点时,我躺在床上,浑身肌肉僵硬,像一具等待行刑的死囚。
来了。“砰!”第一声,像重锤砸在我的心脏上。“砰!砰!”第二声,第三声,连绵不绝,
如同催命的鼓点。那声音不再是单纯的噪音,它仿佛带着王建军那张苍白脸庞上诡异的笑,
带着肉馅飞溅的粘腻触感,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作呕的香气——是的,
不知从第几天开始,我似乎在剁肉声传来的间隙里,
隐约能闻到一股极其细微的、若有若无的肉香。很怪异,不像寻常的猪肉或牛肉,带着点腥,
又有点腻人的甜,还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闻到过。
这念头如同毒蛇,啮噬着我摇摇欲坠的理智。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的限度,在第七天的凌晨,
彻底崩断了。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赤着脚冲进厨房。脑子一片空白,
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叫嚣:让他停下!必须让他停下!否则我会疯掉!一定会!
我摸到那把冰冷的菜刀,握紧刀柄,粗糙的触感反而带来一丝畸形的镇定。然后,
我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冲向门口,一把拉开房门,几步跨到隔壁门前。“王建军!开门!
你他妈给老子开门!”我嘶吼着,声音因为极度愤怒和睡眠不足而沙哑变形。
我用空着的那只手疯狂地捶打着那扇斑驳的旧木门,发出“咚咚”的闷响,
与门内持续不断的“砰砰”剁肉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曲荒诞恐怖的交响。“开门!
听见没有!别剁了!我操你妈!别剁了!”菜刀在我手里反射着楼道里昏暗的声控灯光,
晃动着冰冷的光斑。或许是我的吼叫声和砸门声太过骇人,门内的剁肉声,戛然而止。
整个世界陡然陷入一片死寂。只有我粗重的喘息声在楼道里回荡。几秒钟后,
门锁“咔哒”一声轻响。门,缓缓地开了一条缝。没有看到王建军那张令人厌恶的脸。
门缝里,探出一个小脑袋。是他的女儿。我记得搬来那天见过一次,王建军说她叫妞妞,
六岁。小姑娘很瘦小,总是安安静静的,不怎么说话。此刻,她就站在门缝里,仰头看着我。
楼道的光线很暗,照在她脸上,显得那张小脸愈发没有血色。她的眼睛很大,
瞳孔颜色却很浅,像是两颗蒙了灰尘的玻璃珠,空洞洞的,没什么神采,
直勾勾地盯在我脸上,或者说,是盯在我手里那把菜刀上。我举着菜刀的姿势僵在半空,
满腔的怒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堵在了胸口,喷发不出,也咽不回去,憋得我满脸通红,
模样一定既凶狠又滑稽。妞妞似乎并不太害怕,只是用那种没有焦点的眼神看着我,
看了好几秒钟,才小声地、一字一顿地说:“爸爸在给我做小猪包子。”她的声音很轻,
带着孩童特有的稚嫩,但语调却平铺直叙,没有任何起伏,像是在背诵一句与她无关的话。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
怒火在她澄澈尽管蒙尘的目光和这句稚嫩的话语面前,显得有些无处着落。她顿了顿,
那双玻璃珠似的眼睛转向屋内厨房的方向,然后又转回来,看着我,补充了一句,
声音依旧很轻,却像一根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刺入我的耳膜:“可是,叔叔,
”她歪了歪头,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近乎诡异的困惑,“我们家没有猪啊。”一瞬间,
我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头皮阵阵发麻。没有猪?
那每天凌晨,那沉重的剁刀下,被反复砍剁的……到底是什么?就在这时,因为门被打开,
一股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清晰、浓郁的肉香从屋内飘散出来,直接钻入我的鼻腔。
那香气……温暖的,带着油脂的丰腴,
还有一种……一种我绝对在什么地方闻到过的、特殊的味道!不是单纯的肉香,
里面混杂着某种……某种……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越过妞妞瘦小的肩膀,投向屋内。
客厅没有开大灯,只亮着一盏昏暗的小壁灯,光线勉强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透过客厅,
可以隐约看到厨房的方向。厨房的灯光要亮一些,
一个模糊的身影应该是王建军背对着门口,站在灶台前,
似乎因为我的打扰而暂时停下了动作。灶台上,借着那灯光,我清楚地看到,
那一大盆刚刚剁好的肉馅,就摆在那里。那肉馅的颜色……不是鲜红色,也不是暗红色,
而是一种……诡异的、淡淡的粉红色,甚至在灯光下,泛着一点点难以察觉的、黏腻的光泽。
就是这肉馅,飘出那似曾相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香气。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所有的愤怒、所有的质问,都被眼前这极度不协调的景象和妞妞那句石破天惊的话击得粉碎。
握着菜刀的手,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微微颤抖着。王建军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注视,
他的背影僵硬了一下,然后,极其缓慢地,一点一点地,转了过来……02我握着菜刀的手,
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微微颤抖着。那冰冷的金属触感,
此刻是唯一能让我确认自己还停留在现实的东西。王建军的背影在厨房明亮的灯光下凝滞,
像一尊突然被切断电源的机器。时间仿佛被拉长,每一秒都粘稠得令人窒息。
妞妞依旧仰着头,用那双蒙尘的玻璃珠眼睛看着我,仿佛刚才那句石破天惊的话,
只是随口问了句“吃了吗”。他转过身来了。动作很慢,带着一种刻意的小心翼翼。
他的脸在厨房光线的逆光中显得有些模糊,只能看到大致的轮廓,
以及那双在暗影里似乎格外幽深的眼睛。他先看了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顿片刻,
然后缓缓下移,落在我紧握的菜刀上。他的瞳孔似乎收缩了一下,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没有惊恐,没有愤怒,甚至连一丝被打扰的不耐烦都没有。只有一种……死水般的平静,
或者说,麻木。“妞妞,怎么让客人站在门口?”他的声音依旧是那种带着沙哑的低沉,
听不出情绪。他伸手,轻轻将妞妞往自己身后揽了揽,用一个不算高大的身躯,
将女儿完全挡住,只留下一点点衣角。“林先生,”他的视线重新回到我脸上,
语气甚至带上了一点诡异的歉意,“这么晚了,有事?”有事?我他妈都快被你逼疯了,
你问我有没有事?一股混合着恐惧和被无视的怒火再次冲上头顶,但这次,
它被一种更深的寒意压制着,冲撞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却无法像刚才那样咆哮出来。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得发不出清晰的声音,只能勉强挤出一句:“你……你到底在剁什么?
”我的声音嘶哑,带着自己都没预料到的颤抖。目光不受控制地越过他的肩膀,
死死盯住厨房案板上那一大盆粉红色的肉馅。那颜色太不正常了,
像某种劣质的人造色素调出来的,又像是……被稀释过的血液浸泡过。
浓郁的香气更加直接地扑面而来,钻进我的鼻腔,勾起一种遥远而危险的回忆,
可那记忆的碎片太过模糊,我抓不住。王建军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案板,
脸上那僵硬的表情似乎松动了一丝,嘴角极其轻微地扯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不像。
“肉馅啊。”他回答得理所当然,甚至带着点理所当然的困惑,仿佛我的问题愚蠢至极。
“明天包子铺要用的,吵到你了?真对不住,今天活儿多,耽误了点时间,马上就好了。
”他说话的时候,一只手始终背在身后,似乎握着什么东西。是那把剁骨刀吗?
“没有猪……”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重复了妞妞的话,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
“妞妞说……你们家没有猪……”王建军的身体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一瞬。他低头,
看了一眼躲在他身后的女儿,再抬起头时,眼神里似乎多了点什么,
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像是戒备,又像是……怜悯?“小孩子胡说的。
”他语气平淡地打断我,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终结意味,“林先生,你脸色很不好,
是不是太累了?回去休息吧,我保证,马上就结束。”保证?他之前的保证就是个屁!
我还想再问,想冲进去看个究竟,想用手里这把可笑的菜刀逼他说出实话。
但理智的残丝在最后一刻拉住了我。我闯进邻居家,手持利刃,面对着一个手无寸铁也许?
的男人和他年幼的女儿?这画面太疯狂了。而且,他那种异常的平静,
比歇斯底里更让人心底发毛。就在这时,妞妞从他身后又探出半个脑袋,
那双空洞的眼睛依旧看着我,小声补充了一句:“爸爸说,是秘密。
”王建军轻轻拍了拍女儿的头,没再说话,只是用那种平静得可怕的眼神看着我,
无声地施加着压力。对峙。令人窒息的沉默在楼道和门内之间蔓延。只有那诡异的肉香,
如同实质的触手,缠绕着我,挑逗着我濒临崩溃的神经。我败下阵来。不是被说服,
而是被一种更深沉、更未知的恐惧攫住了。眼前的父女,这凌晨的剁肉声,这粉红色的肉馅,
这熟悉的香气……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個我无法理解、更无法对抗的诡异旋涡。
我喉咙滚动了一下,最终,什么也没说。握紧菜刀的手,无力地垂落下来。
我深深地、带着绝望地看了一眼那盆肉馅,然后,一步一步,僵硬地向后退,
退回了自己的家门。关门,落锁。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手里的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也顺着门板滑坐在地。门外,
一片死寂。他们没有关门吗?还是在透过门缝看着我?几秒钟后,
或许是几分钟后——时间感已经彻底混乱——那熟悉的、富有节奏的“砰砰”声,
再次响了起来。砰!砰!砰!一下,一下,精准地敲打在我的心脏上。它没有变得轻快,
反而似乎……更加沉稳,更加笃定了。仿佛我刚才的崩溃和质问,
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小插曲,丝毫没有影响他既定的流程。我蜷缩在门后,
双手死死捂住耳朵,指甲几乎要掐进头皮。但那声音,那香气它甚至穿透了门板!,
无孔不入。那一晚,后面的时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记忆已经模糊。
只记得自己像个溺水的人,在冰冷的恐惧海洋里沉浮,直到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泛出鱼肚白,
那剁肉声才如同幽灵般悄然褪去。世界重归寂静,但那寂静,比噪音更令人不安。第二天,
我破天荒地请假了。我无法面对工作,无法面对任何人。镜子里的我,眼窝深陷,脸色蜡黄,
嘴唇干裂,活脱脱一个刚从地狱爬出来的难民。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梳理混乱的思绪。
王建军。妞妞。凌晨两点。剁肉馅。粉红色。诡异的香。没有猪。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我脑子里疯狂旋转,却拼凑不出一个合理的图像。
我必须弄清楚那香气是什么!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像一根卡在喉咙里的鱼刺,不拔出来,
我永远无法安宁。我开始在记忆里疯狂搜索。不是菜市场的普通肉腥,
不是饭店后厨的浓郁荤香,也不是某种香料……它更隐秘,更……带着点腥甜,
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仿佛沉淀了很久的……陈旧气息。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像一头困兽般来回踱步。中午的时候,我实在饿得发昏,准备泡碗面应付一下。
拿起热水壶接水时,看着哗哗流出的自来水,一个模糊的念头闪过。水……潮湿……等等!
我猛地停下动作,心脏像是被重锤击中。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
跟着父母回乡下老家过年。老宅后面有个废弃的谷仓,常年锁着。有一次和堂兄弟玩捉迷藏,
我无意中撬开了谷仓角落一个松动的木板,钻了进去。里面堆满了陈年的农具和杂物,
、无法形容的气味——灰尘、霉烂、还有……一种温热的、带着腥臊和一丝怪异甜腻的气味。
堂哥后来找到我,脸色发白地把我拽出来,说那谷仓以前死过一窝刚生下来没多久的猪崽,
大概是病死的,大人图省事就扔里面了,估计早就烂没了。
当时那种混合着腐烂和某种特殊生灵气息的味道,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
以至于很多年都忘不掉。而昨晚,从王建军家里飘出来的那股肉香里,
就隐隐约约带着一丝……一丝那种气味的影子!虽然被烹饪后的香料气息掩盖和修饰了很多,
但底层那股特殊的、属于某种幼崽的、带着点奶腥和怪异甜腻的底味,极其相似!
这个联想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当场吐出来。不,不可能!这太荒谬了!
都过去多少年了,我怎么可能还记得那么清楚?而且,那是死猪崽,这是……这是什么?
“没有猪……”妞妞的话再次在我耳边响起,如同魔咒。如果……如果不是猪呢?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如同藤蔓般疯狂滋长,缠绕住我的心脏,越收越紧。接下来的两天,
我活得像个幽灵。白天精神恍惚,不敢待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