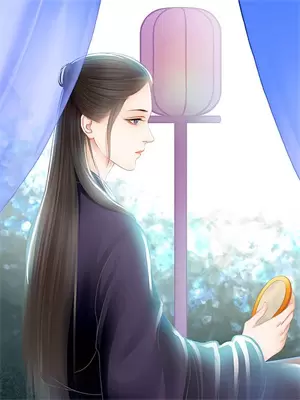王二丫是被一阵刨木头的声音吵醒的。
这声音“咔嗤、咔嗤”的,像是有人在用钝斧头劈骨头,黏腻又滞涩,从后半夜一直响到天蒙蒙亮。她裹紧了补丁摞补丁的被子,缩在炕角,盯着糊着报纸的窗户——窗纸上印着1983年的旧闻,边角都卷了毛边。
她家在村子最东头,孤零零地挨着那棵三人合抱的老槐树。槐树有上百年了,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到房顶上,像只摊开的鬼爪。村里老人说,这树聚阴,晚上不能靠近,可王二丫爹偏不信,说树底下凉快,硬是在树根旁搭了个柴棚。
“爹,你又在劈柴?”二丫哑着嗓子喊,声音被炕洞的烟熏得发涩。
没人应。
刨木头的声音还在响,这次听得更清楚了,像是从柴棚那边传来的。二丫心里发毛,披了件旧棉袄,踩着冻裂的棉鞋往门口挪。门轴“吱呀”一声惨叫,冷风灌进来,带着股铁锈和松木混合的怪味。
柴棚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昏黄的光。二丫扒着门缝往里看——
她爹王老实正背对着她,蹲在地上,手里拿着把锈迹斑斑的刨子,正一下下刨着块棺材板。那木板红漆斑驳,边角却磨得溜光,一看就是放了有些年头的老物件。更瘆人的是,棺材板上还贴着张褪色的红剪纸,剪的是个咧嘴笑的新娘,眼睛却被挖了个窟窿。
“爹,你弄这干啥?”二丫的声音发颤。
王老实猛地回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嘴角却咧着笑:“给你哥备的嫁妆。”
二丫脑子“嗡”的一声。
她哥王大柱前阵子在城里打工,说是认识了个城里姑娘,要娶回家。可哪有给儿子备棺材当嫁妆的?
“爹,你疯了!”
“没疯。”王老实低下头,继续刨棺材板,木屑簌簌往下掉,“那姑娘家说了,就得要这个,不然不嫁。”他说着,拿起那张红剪纸,往棺材板上贴,“你看,多喜庆。”
剪纸新娘的窟窿眼对着二丫,像是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