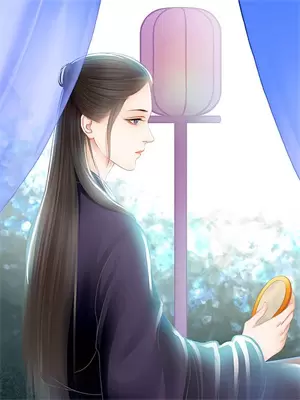槐娘死时,双眼被挖,浑身缠满红绳。村民将她埋在老槐树下,以为邪事已了。第七天,
整个村子开始弥漫槐花香。所有参与挖眼的人,眼皮都长出细密的血丝。血丝一天天变长,
如同槐树根系扎进脑髓。他们相继发疯,用指甲抠烂自己的眼窝。却在镜中发现,
抠出的眼球上浮现着槐娘的笑脸。1 第七日,槐香起第七日,头七,回魂夜。
鸡刚叫过三遍,天色却并未如常亮起,反而被一种粘稠的、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
王家坳醒得格外迟,不是懒,是那股子味道逼得人不敢大口喘气。是槐花香。浓得发腻,
甜中透着一股腐败的腥气,无处不在,从门缝、窗隙、甚至泥土的毛孔里丝丝缕缕钻出来,
织成一张无形无质、却让人胸口发闷的网。这季节,老槐树的花期早过了,更何况,
村里唯一那棵老槐树下,七天前才埋下那个不祥的女人。李老栓是第一个察觉不对的。
七天前,正是他,手里握着那柄磨得雪亮的剔骨刀,在众人的按捺下,
剜出了槐娘那双据说能勾走男人魂魄的桃花眼。此刻,他躺在炕上,眼皮火烧火燎地痒,
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在薄薄的眼皮底下爬。他用力揉搓,越揉越痒,痒得钻心,
恨不得用指甲去抠。“作死啊!揉什么揉!”他婆娘被吵醒,没好气地嘟囔,翻了个身。
可当她借着从糊窗纸破洞透进的微光瞥见李老栓的脸时,一声尖叫卡在了喉咙里。
李老栓的眼皮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鲜红的细丝,像刚刚织就的蛛网,
又像老槐树裸露在地表的根系,虬结着,隐隐还在搏动。那红丝正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
缓慢地向着四周的皮肤蔓延。“鬼……鬼啊!”婆娘连滚带爬跌下炕,指着李老栓,
浑身抖得像筛糠。李老栓冲到屋里那面模糊的铜镜前,只看了一眼,
一股寒气就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镜子里那张脸,眼皮上爬满了妖异的红网,
而那红网的源头,似乎正连着瞳孔深处。他猛地想起埋槐娘时,
她身上缠满的那些浸过黑狗血、据说能镇魂的红绳。当时他还觉得里正太过小心,
一个被挖了眼的女人,还能翻起什么浪?现在,那红绳的诅咒,仿佛通过这诡异的血丝,
缠到了他的眼皮上。与此同时,王家坳另外几户人家的院子里,
也相继爆发出类似的惊惧哭嚎。参与过那夜暴行的,无论是动手挖眼的,
还是仅仅在一旁按过手脚、递过绳子的,无一例外,眼皮上都开始浮现那诅咒般的血丝。
2 生根恐慌像瘟疫一样,在弥漫的槐花香中迅速传开。
里正王老贵召集了那夜所有去过老槐树下的人,连他在内,一共九个。祠堂里,
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往日里这些在村里作威作福的男人们,此刻个个面如死灰,
眼神躲闪。他们互相打量着对方眼皮上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的血色网络,
恐惧在无声中交换、滋长。“肯定是那妖女作祟!”王老贵强作镇定,拍着桌子,
“我已经派人去五十里外的青云观请张天师了!大家稳住,别自乱阵脚!
”李老栓却没那么乐观。他感觉那血丝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们像活的虫子,
正一点点往肉里钻,往骨头里扎。痒劲过去后,是一种细微却持续的刺痛,
仿佛有无数根极细的针,顺着眼周的血管,朝着脑袋深处刺去。他夜里开始做噩梦,
梦见自己躺在老槐树下,泥土埋到胸口,槐树的根须像毒蛇一样从四面八方钻过来,
缠住他的脖子,刺破他的眼皮,直直扎进他的眼珠,贪婪地吮吸着。白天,他精神恍惚,
耳边总响起槐娘被挖眼时,
那凄厉到不似人声的诅咒:“你们挖我的眼……我要你们……世世代代……永不见天日!
”第三天,铁匠赵大力先疯了。他是个莽夫,那夜按着槐娘腿脚的就是他,使得力气最大。
血丝在他眼皮上长得也最快,已经蔓延到了颧骨和眉心,颜色变得暗红发黑。
他先是胡言乱语,说看见槐娘在炉火里对他笑,
接着就开始用那双打铁的大手疯狂抓挠自己的眼睛,指甲在脸上划出一道道血痕,
旁人拉都拉不住。最后,他一头撞死在烧红的铁砧上,焦糊的肉味混合着槐花香,令人作呕。
赵大力的死,彻底击溃了众人的心理防线。请来的张天师倒是来了,穿着八卦道袍,
手持桃木剑,在老槐树下做法事。符纸烧了,圣水洒了,铃铛摇得山响。
可那槐花香非但没减,反而更浓了。张天师最后盯着那棵沉默的老槐树,脸色煞白,
收起法器,对王老贵拱拱手:“此怨念太深,已与地脉邪气相连,非贫道所能化解,
诸位……好自为之。”说罢,竟头也不回地走了。希望破灭,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
淹没了剩下的八个人。3 疯魔血丝在继续生长。它们不再满足于眼皮,
开始像真正的植物根系一样,向下巴、脖颈,甚至向头皮深处延伸。
那种刺痛感也越来越强烈,变成了持续的、钻凿般的疼痛,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
仿佛真的有槐树的根须在颅内生长,搅动着脑髓。屠夫孙癞子第二个撑不住了。
他变得极度狂躁,砸烂了家里所有能映出人影的东西,包括一面他婆娘陪嫁的玻璃镜。
但他无法逃避水缸里的倒影,无法逃避任何光滑表面反射出的,那张被血色根系侵蚀的脸。
他开始出现幻觉,总说槐娘就站在他身后,用那双空洞流血的眼窝盯着他。一天清晨,
他婆娘发现他蜷缩在墙角,双手死死抠进了自己的眼窝,
两个血糊糊的眼球被他生生抠了出来,扔在地上,脸上却带着一种诡异而解脱的笑容。
他没死,但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整天在村里游荡,发出嗬嗬的怪笑。
接着是王老贵的儿子王福,那夜他只是跟在父亲身后,壮胆助威,甚至没敢靠近槐娘的尸体。
可诅咒并未因此放过他。这个平日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极度的恐惧和疼痛折磨下,
变得痴痴傻傻,最后用一根麻绳,把自己吊死在了房梁上。死亡以各种方式降临。有人投井,
有人跳崖,有人像赵大力一样自残而死。村子里风声鹤唳,家家闭户,白天也听不到人声,
只有那永恒的、甜腻的槐花香,和偶尔从某户人家传出的凄厉惨叫或疯狂呓语。
李老栓还硬撑着,但他知道,自己也快到头了。他感觉自己的脑袋越来越沉,像灌满了铅,
又像塞满了盘根错节的树根。视线开始模糊,看什么东西都蒙着一层血红色的薄雾。
疼痛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的神经,他几乎无法入睡,
一闭眼就是槐娘那张惨白的脸和流血的眼窝。4 镜中笑第九天夜里,风雨大作。
电闪雷鸣中,老槐树的影子在窗外张牙舞爪,像极了索命的恶鬼。李老栓蜷缩在炕角,
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被,却依然冷得牙齿打颤。他婆娘早就带着孩子躲回娘家去了,
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屋里的油灯早就熄了,黑暗中,只有闪电划过的瞬间,
才能短暂地照亮屋内的轮廓。一道惨白的电光闪过,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声。
就在那电光石火间,李老栓的眼角余光,
瞥见了墙角立着的那面被他婆娘藏起来、却被他偷偷找出来的旧铜镜。镜子里,
映出一张鬼一样的脸——那是他的脸。眼皮、脸颊、额头,甚至鼻孔和嘴角边缘,
都布满了暗红色的、粗壮如同蚯蚓的“根系”,这些根系还在微微搏动。而他的双眼,
因为长期的痛苦和恐惧,布满了血丝,几乎看不到眼白。不,那不是血丝。
李老栓猛地扑到镜子前,几乎将脸贴在了冰凉的铜面上。他死死盯着镜中自己的眼睛。
在那些密集的、属于他自己的红血丝深处,他看到了别的东西。是槐娘!不是幻觉,
是真真切切地映在镜子里!就在他浑浊的眼球瞳孔的倒影中,浮现着槐娘那张脸!
眉眼依旧精致,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但那笑意冰冷刺骨,充满了怨毒和嘲讽。
她的眼窝不再是空洞的血洞,而是变成了两汪深不见底的幽潭,仿佛要将他的魂魄吸进去。
“啊——!”李老栓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嚎叫,压过了窗外的雷声。
极致的恐惧瞬间冲垮了他最后一丝理智。那扎根在脑髓深处的剧痛和瘙痒,
以及镜中槐娘那诡异的笑脸,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挖掉!挖掉就不痒了!
挖掉就看不见了!”一个疯狂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尖叫。
他伸出颤抖的、指甲缝里满是泥垢的双手,十指弯曲成爪,用尽全身的力气,
狠狠地抠向自己的双眼!剧痛袭来,温热的、粘稠的液体喷溅而出,糊了他一脸。
但他却感觉不到疼痛似的,反而有一种扭曲的解脱感。他疯狂地抠挖着,撕扯着,
直到将两个眼球连带着一些黏连的神经组织从眼眶里硬生生扯了出来!
“嗬……嗬……”他喘着粗气,脸上血肉模糊,只剩下两个不断淌血的窟窿。
他将那两颗还在微微颤动、沾满鲜血的眼球捧到眼前——尽管他已经看不见了。就在这时,
又一道闪电亮起。凭借那瞬间的光亮,透过满手的鲜血,
李老栓那已经失去视觉、却仿佛被某种力量强行灌注了“景象”的脑海中,
清晰地“看”到了——在他掌心那两颗血淋淋的眼球光滑的晶状体表面上,
槐娘那张带着温柔浅笑的脸,正静静地“看”着他。笑容依旧,甚至比刚才在镜中看到的,
更加清晰,更加真切。那笑容,仿佛在说:看,我们终于一样了。李老栓僵在原地,
捧着自已眼球的双手剧烈颤抖,然后,他仰天发出一串断续而癫狂的笑声,最终气绝身亡,
倒在血泊中,脸上定格着极致的恐惧和那抹挥之不去的、来自眼球倒影中的诡异笑容。
5 槐花开不尽风雨渐歇,天快亮了。王家坳死一般寂静。参与那场暴行的九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