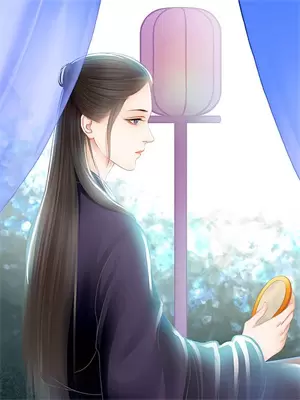1我签下名字时,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噪音,像在割裂我仅存的希望。对面,
穿白大褂的张医生推了推眼镜,眼神里的职业性同情混着无能为力,看得我心口发闷。
“陈先生,这是第三次实验性治疗方案了。说实话,我们对您母亲的病症……依然没有头绪。
”“枯萎病”,这是我私下给母亲的病起的名字。
医学上那串“成因不明的进行性全身器官衰竭”的诊断太冰冷,在我眼里,
母亲明明就像一株被抽干水分的植物。她的皮肤没了光泽,一天比一天暗沉;头发大把脱落,
露出苍白的头皮;最让我心惊的是她的手——那双曾为我缝补衣物、做过无数顿热饭的手,
如今干枯得像老树枯枝,青色血管在薄如蝉翼的皮肤下虬结,仿佛下一秒就会爆裂。
“她只是在……枯萎。”我曾这样跟医生描述,换来的只有对方困惑又怜悯的目光。
所有检查数据都指向一个缓慢却不可逆的终点,仪器上的曲线,
就是给母亲生命下的冷酷判决书。我耗尽了积蓄,也耗尽了现代医学能给的所有希望。昨晚,
我守在重症监护室外,隔着玻璃看沉睡的母亲。监护仪的滴滴声单调而规律,
像枚冰冷的秒表,在为她的生命倒数。就在绝望快要将我淹没时,母亲的嘴唇忽然翕动起来。
我立刻凑到玻璃前,拼命分辨那微弱的气音。“锁龙镇……老井……”断断续续的几个字,
像从极深极远的地方传来,带着梦呓般的执着。“妈?你说什么?”我拍打着玻璃,
可母亲又陷入了沉寂。“锁龙镇”,这个地名像把生锈的钥匙,
捅开了我记忆深处的尘封之门。那是我的故乡,五岁时随父母离开的偏远山村,
地图上都快找不到标记。我只剩些模糊印象:潮湿的青石板、总弥漫雾气的山峦,
还有一个黑洞洞的井口。我不知道母亲弥留之际为何念叨这里,但我像溺水的人,
死死抓住了这根不知从何而来的稻草。第二天,我办了暂缓治疗的手续,
无视医生“这很危险”的警告,买了去最近县城的火车票。我必须回去,
看看那口被母亲挂在嘴边的老井,到底藏着什么。2从县城转乘唯一一班进山的长途汽车,
一路颠簸着,窗外的景色从平整柏油路和现代建筑,变成蜿蜒土路和连绵青山。
空气里渐渐飘来潮湿泥土与腐木混合的气息,陌生又熟悉。“锁龙镇,到了!
”司机不耐烦的喊声响起时,我才发现车上只剩我一个乘客。跨下车门,
脚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凉意顺着脚底瞬间窜遍全身。这就是锁龙镇。
和记忆里的碎片一模一样,这里仿佛被时间遗忘了。天色阴沉,厚重的云层压得很低,
细密雨丝若有若无地飘着,给整个村子蒙了层灰色滤镜。房屋多是黑瓦青砖的老结构,
墙壁爬满青苔,像长了霉斑的旧衣。村子安静得诡异。明明是下午,却几乎看不到人影,
连鸡鸣犬吠都听不见。只有风穿过窄巷时,发出呜呜的声响,像不知名生物在低语。
偶尔有村民从门缝里探出头,看我的眼神混着好奇、警惕,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躲闪。
那目光不像看归乡游子,倒像看一个不该出现的闯入者。凭着模糊记忆,我找到了祖宅。
院门上的铜锁早锈死了,我费了好大劲才用石头砸开。推开门的“吱呀”声惊起一片灰尘,
院子里杂草齐腰高,荒芜得让人无处落脚。我没心思收拾,
径直往村子中心走——我要找刘叔,村里辈分最高的长辈,也是我家远房亲戚。
刘叔家就在村口大槐树边。他坐在门口,手里捏着烟杆,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
他比我记忆里老了太多,背驼了,脸上刻满沟壑般的皱纹。看到我,
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黯淡下去。“是……阿默啊。”他声音沙哑。“刘叔。
”我走上前,开门见山,“我回来是想问您,关于村子中心那口老井……”话音未落,
刘叔的脸色骤然一变。他猛地挺直佝偻的背,眼神变得异常锐利,
死死盯着我:“谁让你问这个的?你回来干什么!”这反应远超我的预料,我愣了愣,
说:“我妈病了,很重。她昏迷的时候,一直在念叨这里的老井。”刘叔脸上的肌肉抽了抽,
眼神里的锐利褪去,换上深不见底的忧虑和悲哀。他把烟杆往门槛上磕了磕,烟灰簌簌落下。
“糊涂啊……你妈她糊涂啊!”他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近乎警告,“阿默,听叔一句劝,
回城里去,就当没回来过。那口井,碰不得。”“为什么?”我追问,“那只是一口井而已。
”“井?”刘叔冷笑一声,笑声里带着寒意,“那不是井,是个债主。你跟它许愿,
它就得收账。那账……你还不起!”他举起左手,袖管空荡荡的,在风里飘着。“看到没?
这就是还的账。”我心头一震,却强迫自己冷静——我是个建筑设计师,信科学和逻辑,
不信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刘叔,我需要知道真相。我妈快不行了。
”刘叔定定看了我许久,最终像是放弃了劝说。他疲惫地摆了摆手:“村子正中心,
你自己去看吧。但记住叔的话,别跟它说话,别对它有任何念头。看一眼,就赶紧走。
”3夜幕降临,锁龙镇更死寂了。雨似乎停了,可空气里的湿气更重,
凝结成薄雾在巷道间缓缓流动。我独自坐在破败的祖宅里,手机屏幕亮着,
是护士刚发的消息:陈先生,您母亲的血氧饱和度在持续下降,建议您尽快回来。
冰冷的文字像锤子,敲碎了我最后一丝理智。
刘叔白天的警告、那空荡荡的袖管在脑海里闪过,恐惧和怀疑交织着,
可母亲在监护室里“枯萎”的样子,终究压倒了一切。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要试。
抓起外套走出院子,村子中心不难找。穿过几条窄巷,一片小空地出现在眼前,
中央就是那口老井。它比我想象的更古老,也更诡异。井口是巨大青石垒成的,
石壁上布满风雨侵蚀的痕迹和厚厚的青苔。凑近了,能闻到泥土混着铁锈的腥冷气息,
仿佛井下藏着某种古老生物,在缓缓呼吸。井口直径不过一米,朝里望去黑不见底。
一层乳白色雾气缭绕在井口,像有生命般盘旋。我甚至产生错觉,雾气之下,
有双眼睛在窥视我。环顾四周空无一人,远处几户人家的窗户透出微弱摇曳的灯光,
像警惕的眼睛。我想起刘叔的话:“别跟它说话。”犹豫涌上心头。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对着一口井许愿,太荒谬了。我都能想象出同事们嘲笑的表情。
可就在这时,手机震动起来,是医院的电话。我不敢接,
任由那催命般的铃声在死寂的夜里一遍遍响起,直到自行停下。铃声停了,
我的心理防线也彻底崩了。我趴在冰冷的井沿上,把头探向黑暗。腥冷气息扑面而来,
让我打了个寒颤。心跳声擂鼓般响着,我闭上眼,又看到了母亲那双干枯的手。
“我希望……”我开口,声音沙哑微弱,像怕惊扰了什么,“我希望……我母亲能好起来,
哪怕只是一点点。”声音被井里吸走,没有一丝回响。说完,我像耗尽全身力气,
瘫坐在井边。四周依旧死寂,井口的雾气还在盘旋,什么都没发生。
巨大的失落和自嘲涌上来,我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傻瓜。摇摇晃晃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我转身往祖宅走。决定天一亮就回城,接受现实。可就在转身的刹那,
我似乎听到井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轻得像错觉。我猛地回头,井口依旧,
只有雾气在无声翻滚。4我几乎一夜未眠,在布满灰尘的旧木板床上辗转反侧。
天蒙蒙亮时才迷迷糊糊睡去,却被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心脏猛地一缩,
以为是医院来报丧的。我颤抖着手划开接听键,做好了接受最坏消息的准备。“陈先生吗?
我是ICU的王护士!”电话那头的声音满是压抑不住的惊喜,“奇迹!真是奇迹!
您母亲今天早上自己醒了,精神特别好!刚刚还喝了一小碗粥!各项生命体征都在回升!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怀疑自己还在梦里。“……你说什么?”“您母亲好转了!
非常明显的好转!张医生也说不可思议!您要不要跟她说几句话?”电话很快交到母亲手里,
听筒里传来她虚弱却清晰的声音:“阿默……妈没事了……你别担心……”那一刻,
眼泪夺眶而出。巨大的喜悦冲垮了所有理智和怀疑,我对着电话连声说好,挂断后冲出屋子,
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大吼一声,要把这段时间的压抑全宣泄出来。是那口井!一定是那口井!
我欣喜若狂,甚至想立刻跑到井边磕几个头。昨晚的荒唐,此刻看来无比明智。
什么科学逻辑,在母亲的生命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我兴奋地在村里转悠,
想找人分享这份喜悦。可走到邻居王婶家门口时,却听见里面传来凄厉的哭喊。走近一看,
王婶瘫坐在鸡窝旁,一边拍大腿一边嚎啕:“我的‘福星’啊!我的下蛋金鸡啊!
怎么就……怎么就一夜之间变成这样了啊……”我认得那只鸡。是王婶的宝贝,据说通人性,
还几乎每天下双黄蛋,都十几年了,在村里传为奇事,被她当成家里的“福星”。
我上前想安慰几句,目光却不由自主落在那只死鸡上。它干瘪、毫无生气,羽毛黯淡无光,
像是被抽干了所有生命力。我的心猛地一沉。这只鸡的样子,和母亲病重时的“枯萎”状态,
何其相似!一个可怕的念头像冰冷的毒蛇,从心底钻出来。我想起刘叔的话:“那不是井,
是个债主。”难道……母亲的好转,是用这只鸡的命换的?我强迫自己甩掉这个荒唐的想法。
怎么可能?一只鸡的命,怎么能和人的生命相提并论?这一定是巧合,绝对是巧合。
安慰了王婶几句,我落荒而逃般回到祖宅。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母亲的好转是医学奇迹,
和鸡的死没关系。可只要一闭眼,那只干瘪的鸡和母亲病床上的面容就重叠在一起。
一种冰冷黏腻的恐惧,悄悄缠上了我的心脏。5母亲的好转没持续太久。一周后,
我再回医院,发现她虽脱离生命危险,整个人却陷入奇怪的停滞。能自己吃饭,能简单对话,
可眼神空洞,行动迟缓,像被勉强注入活力的木偶。她不再“枯萎”,也没恢复生机,
就像株移栽到贫瘠土壤的植物,仅维持不死。张医生找我谈话,表情严肃:“陈先生,
你母亲情况特殊。指标都稳定,却没进一步好转迹象。我院专家组讨论后,
建议尝试国外引进的基因干预疗法。这是最前沿技术,但……”他顿了顿,语气为难,
“费用很高,一个疗程七位数,成功率也没法保证。”七位数,像座大山压在我胸口,
让我喘不过气。我刚耗尽积蓄,还欠着朋友钱。夜里,我独自坐在医院冰冷的长椅上,
手机屏幕光照亮憔悴的脸。屏幕上是母亲年轻时抱我的照片,笑得灿烂。我摩挲着笑脸,
内心天平剧烈摇摆。王婶家干瘪的死鸡,刘叔飘荡的空袖管,像幽灵在脑海反复闪现。
理智声嘶力竭警告:那口井是魔鬼契约,沾不得。可紧接着,
母亲病床前微弱的呼吸、空洞的眼神,又像重锤敲打着心脏。我想起跪在病床前,
拉着她干枯的手发誓要治好她的情景。“就算是真的又怎样?”心底一个阴冷的声音响起,
像毒蛇吐信,“一只鸡的命,怎么能跟我妈的命比?不过一个畜生,
难道比我妈的命还重要吗?”理智堤坝一出现裂缝,欲望洪水便奔涌而入。
我尝过“奇迹”的甜头,那种攥住命运的感觉,让我无法忍受束手无策的无力。
我甚至为自己找借口:这是等价交换,用微不足道的东西换至亲生命,天经地义。
这念头一旦产生,便如野草疯长。我欺骗自己,或许那井没那么邪恶,只是遵循古老规则。
只要付出的“代价”是别人家无关紧要的东西,就没什么大不了。当晚,我找借口离开医院,
连夜驱车,再次回到阴湿的村庄。第二次站在井边,我没了初时的恐惧和犹豫。
夜风依旧冰冷,井口雾气依旧诡异盘旋,可在我眼中,它成了能满足一切欲望的万能宝库。
我眼神里只剩近乎疯狂的决绝。俯身对着漆黑的井口,不再小心翼翼祈求,
而是像对合作伙伴下订单,语气清晰坚定:“我需要钱,一大笔钱,足够治好我母亲的病。
”说完,我直起身,没片刻停留,转身就走。甚至没回头再看井一眼,
仿佛只是完成桩平常交易。6第二天一早,我回到祖宅。
找借口继续向公司请长假应付治疗时,翻找旧物想找证明与这里渊源的文件,
手无意中敲了敲堂屋墙壁。“咚咚”,墙壁发出空洞回响。我心中一动,找来锤子,
对着那块地方用力砸下去。几下后,石灰和泥土簌簌落下,露出黑漆漆的洞口。洞里,
一个被油布包裹的铁盒静静躺着。心脏狂跳,我把铁盒取出来。盒子很沉,锁早已锈死。
用锤子暴力砸开,“哐当”一声,一片耀眼的银光瞬间晃了眼。
盒子里装满码放整齐的“袁大头”,银元下还压着几件金首饰——一个镯子,两枚戒指,
还有一个长命锁。巨大的狂喜攫住了我。把冰凉的贵金属一股脑倒在落满灰尘的桌上,
昏暗屋里它们闪烁着醉人的光芒。拿起一枚银元,感受沉甸甸的份量,
上面的头像在微光下栩栩如生。井,真的回应了我!还如此迅速、慷慨!粗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