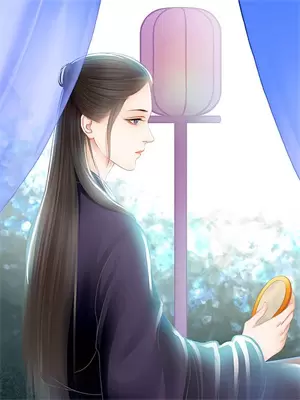外卖员送餐遇到艳遇的短剧
作者: 七斤烈酒悬疑惊悚连载
《外卖员送餐遇到艳遇的短剧》中的人物苏晚陆文拥有超高的人收获不少粉作为一部悬疑惊“七斤烈酒”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不做以下是《外卖员送餐遇到艳遇的短剧》内容概括:那个雨我接了个送往山顶别墅的订开门的是个只穿丝绸睡袍的女她指尖掠过我淋湿的制服:“外面进来擦”室内弥漫着昂贵香水与孤独交织的气她让我用身体暖她冰凉的却在触碰瞬间落泪:“三年你是第一个碰我的”后来才知这栋别墅没有女主人——只有个被囚禁的金丝而送餐箱底藏着前一位外卖员干涸的血雨下得像是天漏不是那种温柔的、富有诗意的淅淅沥而是蛮横的、砸碎一切宁...
那个雨夜,我接了个送往山顶别墅的订单。开门的是个只穿丝绸睡袍的女人,
她指尖掠过我淋湿的制服:“外面冷,进来擦擦。”室内弥漫着昂贵香水与孤独交织的气息。
她让我用身体暖她冰凉的脚,却在触碰瞬间落泪:“三年了,你是第一个碰我的人。
”后来才知道,这栋别墅没有女主人——只有个被囚禁的金丝雀。而送餐箱底层,
藏着前一位外卖员干涸的血迹。雨下得像是天漏了。不是那种温柔的、富有诗意的淅淅沥沥,
而是蛮横的、砸碎一切宁静的瓢泼。豆大的雨点密集地夯击着柏油路面,溅起半尺高的水汽,
整个世界泡在一片喧嚣的、湿冷的混沌里。路灯的光晕在雨幕中化开,
成了一团团模糊昏黄的斑点,勉强勾勒出空荡街道的轮廓。陆文的电动车前灯,
像两柄疲惫的短剑,勉强劈开这重重雨帘。雨水顺着他的头盔面罩往下淌,
留下蜿蜒扭曲的水痕,外面的景物隔着一层水膜,晃动,变形。防水外套早已失了效,
湿冷紧紧贴着他的皮肤,汲取着那点可怜的热量。手指在湿透的手套里泡得发白、起皱,
僵冷地扣着车把,每一次刹车,都能感到骨头缝里透出的酸疼。手机架在车头,屏幕亮着,
导航地图上,代表他自己的那个蓝色箭头,正沿着一条越来越细、越来越蜿蜒的山路,
艰难地向上爬。订单目的地——“栖霞路77号,听涛苑”——像一枚冰冷的烙印,
钉在屏幕顶端。这单有点邪门。距离远,路偏,又是这种鬼天气。平台加的补贴不算少,
但几乎没人愿意接。他刚送完上一单,在商圈附近的骑手休息点躲雨,
看着奖励金额一点点往上跳,直到跳到一个让他无法忽视的数字,才咬咬牙,点了抢单。
电动车马达发出沉闷的呜咽,负重般爬着坡。山路一侧是湿漉漉的、黑黢黢的岩壁,另一侧,
越过模糊的护栏,是深不见底、被雨水和夜色吞没的空虚。轮胎碾过积水的坑洼,
溅起浑浊的水花。周围寂静得可怕,只有风雨声,以及车轮压过湿滑路面的黏腻声响。
越往上,路灯越稀疏,间隔越远,光线也愈发昏暗。道旁树木的枝桠在风里张牙舞爪地晃动,
投下幢幢黑影,像是蛰伏的活物。终于,导航女声毫无感情地宣布:“您已到达目的地,
目的地在您左侧。”陆文刹住车,单脚支地,抹了一把面罩上的雨水,抬头望去。铁艺大门,
高大,森然,缠枝花纹复杂而冰冷,顶端是尖锐的矛头。透过湿漉漉的铁栏缝隙,
能看到一条宽阔的车道通向远处一栋庞大建筑的轮廓,那轮廓在雨夜中显得沉默而傲慢。
门旁的水泥柱上,嵌着一个不起眼的黑色门铃面板。他停好车,
从保温箱里取出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餐袋。奇怪,这单食物不多,却异常沉重,
入手沉甸甸的,包装也格外精致,不像普通外卖。他没多想,走到门柱前,伸手按向门铃。
指尖还没触到,旁边一个摄像头却无声地转动起来,红色的光点在他身上扫了一下。随即,
“咔哒”一声轻响,大门缓缓向内滑开,露出刚好容一人通过的缝隙。自动化的大门,
监控探头。陆文心里那点异样感又浮了上来。他推着车进了门,沿着车道往前走。
车轮在湿漉漉的砾石路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离那栋建筑越来越近,
才看清是栋灰白色的三层别墅,线条简洁利落,透着一种冷硬的现代感。
巨大的落地窗占据了大部分墙面,但此刻都被厚重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没有一丝光透出来。
整栋房子,只有门口上方一盏壁灯亮着,投下一小圈惨白的光晕,
照亮了门前几级台阶和一根粗壮的罗马柱。太安静了。除了风雨声,再没有别的声响。
这房子里,真的有人吗?他把车停在廊檐下,尽量避开直接淋雨的地方,
深吸了一口湿冷的空气,走到厚重的深色木门前。门上没有门铃,只有一个精致的黄铜门环。
他犹豫了一下,抬手敲了敲门。叩门声在空旷的廊下显得异常突兀,甚至带着点回声,
随即又被风雨声吞没。等了几秒,没有任何动静。他再次抬手,这次用力了些。
门内传来极轻微的“咔哒”声,像是锁舌收回。然后,门被拉开了一道缝。首先涌出的,
是一股暖香。不是寻常人家那种饭菜香或花香,而是一种极其馥郁、层次复杂的香气,
带着点慵懒的甜,又混着一丝清冽,像夜晚盛放的昙花,又带着点皮革与旧木的底蕴,
丝丝缕缕,瞬间驱散了门外的湿冷寒气。门缝后,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丝绸睡袍,长及脚踝,光泽流动,像一池深潭的水。
睡袍的带子系得松松垮垮,领口微敞,露出一段纤细得惊人的锁骨和一抹白皙的肌肤。
她的头发是漆黑的,随意地披散在肩头,有些凌乱,几缕发丝黏在略显潮湿的额角。
她的脸很小,在门厅昏暗的光线下,皮肤白得近乎透明,一双眼睛尤其引人注目,大而黑,
瞳孔深处却像是蒙着一层水汽,空洞洞的,没有任何焦点,只是茫然地朝着门外的方向。
陆文愣了一下,赶紧低下头,双手递上餐袋:“您、您的外卖。”女人没有立刻接。
她的视线,或者说她那没有焦点的目光,缓缓地从他湿透的、还在往下滴水的头盔,
移到他紧裹着湿冷防水外套的身体,最后落在他那双沾满泥浆、鞋面完全湿透的旧运动鞋上。
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带着一种久未开口的沙哑,像羽毛拂过听者的心尖,
却又有种奇异的穿透力,盖过了门外的雨声:“外面冷,”她说,“进来擦擦吧。
”陆文完全僵住了。进来?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平台有规定,骑手不能进入顾客室内。
而且,这女人......她的状态,这栋房子的氛围,都让他心里警铃大作。
“不、不用了,女士。平台规定......”他试图拒绝,
声音因为寒冷和紧张而有些发紧。女人却像是没听见,或者说,不在意。
她那只没有扶门的手抬了起来,指尖纤细,白皙得能看到淡青色的血管。那指尖,
带着一点微凉的、若有若无的触感,轻轻掠过他外套袖口上凝聚的一颗将滴未滴的水珠。
水珠滚落,砸在光可鉴人的入口地砖上,洇开一小团深色。她的指尖停在那里,没有收回。
陆文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窜上来,不是室外的寒冷,而是另一种更诡秘的东西。
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脚跟磕在湿滑的廊檐地面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我......我真的该走了。”他坚持着,声音更干涩了,再次把餐袋往前递了递,
几乎要碰到她睡袍的衣角。女人的手缓缓垂了下去。她沉默了几秒,
那双空洞的眼睛依然朝着他的方向,里面没有任何情绪,像两口枯井。然后,
她极轻微地侧过身,让开了门口的空间。那股暖香更加浓郁地扑面而来,
混杂着房子里某种难以言喻的、陈旧的空旷气息,像是一座久未开启的古墓,
突然泄出了一口积郁的芬芳与寂寥。陆文的脚像被钉在了原地。
理智告诉他必须立刻转身离开,骑上他的车,冲下山,
回到他那虽然破旧但熟悉安全的出租屋。但身体却不听使唤,那暖意,那香气,
种更深沉的、被这雨夜和这女人的异常所勾起的疲惫与......某种他不敢深究的好奇,
像无形的丝线,缠绕着他的四肢。他看着她侧身站立的身影,在睡袍下显得那么单薄,
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她微微低着头,漆黑的长发遮住了她部分脸颊,
只露出一个线条优美的、带着难以言喻的落寞与脆弱的下颌。鬼使神差地,他抬起脚,
迈过了那道高高的门槛。鞋底沾着的泥水和雨水,在光洁如镜的深色大理石地板上,
留下了几个清晰而刺眼的污浊脚印。门在他身后,无声地、沉重地合拢了。
门在陆文身后合拢的瞬间,世界仿佛被隔绝了。震耳欲聋的雨声变得沉闷,
像是从极远的地方传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死寂的静谧,
以及那股无处不在、甜腻得让人有些头晕的暖香。玄关宽敞得惊人,
地面是冰冷的黑色大理石,光洁得能映出他狼狈不堪的倒影。
几盏嵌入天花板的射灯投下锥形的、界限分明的光晕,
照亮了墙上几幅抽象的、色彩阴郁的油画,以及一个摆放着扭曲金属雕塑的壁龛。
一切都极尽奢华,却感受不到丝毫“家”的温暖,
更像是一个设计精良、但无人居住的展示空间。女人——苏晚,
她刚才似乎低语过这个名字——赤着脚,走在大理石地面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墨绿色的丝绸睡袍随着她的步伐微微飘动,像夜色中流淌的溪水。“把东西放在那里吧。
”她指向玄关尽头一个同样由黑色大理石打造的置物台,声音依旧轻飘飘的。
陆文依言走过去,将沉重的餐袋小心放下。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快速扫视着周围。
巨大的客厅连接着玄关,同样是以深色调为主,家具线条简洁而冰冷,
巨大的落地窗被厚重的深灰色窗帘遮得密不透风。他注意到,窗户的锁扣似乎是特制的,
比他见过的任何家用窗户锁都要复杂、坚固。“擦一擦。”苏晚不知何时走近,
递过来一条柔软的白色毛巾。毛巾带着和她身上相似的香气。“谢谢。”陆文接过毛巾,
有些局促地擦拭着头发和脸上的雨水。湿冷的布料离开皮肤,被室内的暖意包裹,
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他脱下湿透的外套,犹豫了一下,没有地方放,
只好尴尬地拎在手里。苏晚看着他,
那双空洞的大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丝极淡的、难以捉摸的情绪。
她指了指客厅里一张巨大的、看起来价格不菲的灰色天鹅绒沙发。“坐吧。
”“我......我身上湿,就不坐了。”陆文站着没动。平台的规则、此地的诡异,
都像警铃在他脑子里回响。但他双脚如同灌铅,
那暖意和眼前女人身上散发出的、浓得化不开的孤独与脆弱,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引力场,
让他无法轻易挣脱。“没关系。”苏晚自己先走到沙发边,蜷缩着坐了下来,双腿收拢,
双臂环抱住自己,下巴搁在膝盖上。这个姿势让她看起来更小了,
像一只受惊后寻求自我保护的小动物。“这里......很少有客人。”陆文沉默着。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问她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这里?问她为什么邀请一个陌生外卖员进门?
这些问题都太唐突,也太危险。“雨很大。”他最终干巴巴地说了一句,目光落在自己脚下。
那几个泥水脚印在光洁的地板上显得格外刺眼。“是啊,很大。”苏晚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嘴角似乎极轻微地牵动了一下,像是笑,又不像。“这房子,平时很安静。
安静得......能听见灰尘落下的声音。”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梦呓般的质感。“有时候,
我会站在窗边,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或者......偶尔经过的车声。
那是外面世界的声音。”她抬起头,视线没有焦点地投向那厚重的窗帘,
“‘他’不喜欢吵闹,也不喜欢光。所以,窗帘总是拉着。”陆文的心跳漏了一拍。“他”?
“他......是你的先生?”陆文试探着问,声音不自觉地压低。
苏晚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环抱着自己的手臂收得更紧了。她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喃喃道:“他说,这里安全。安静,适合我。”她顿了顿,像是在回忆什么久远的事情,
“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又真慢。”三年。这个数字再次出现,
像一把小锤子敲在陆文的心上。他想起她开门时说的那句话——“三年了,
你是第一个碰我的人。”一种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这不是寻常夫妻的生活状态。